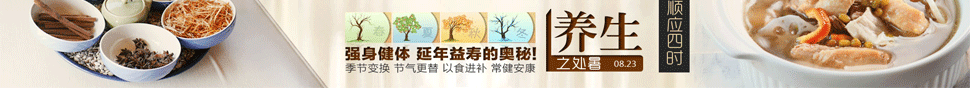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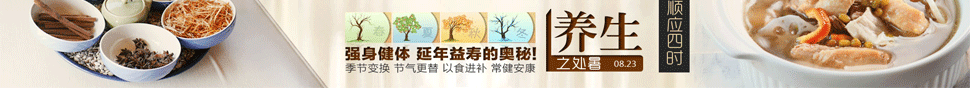
年第期(总第期)
童年的记忆
王秀琴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我出生在北京昌平区东小口,东小口车站东小口村的一个四合院里。在那个四合院里我和我的父亲、母亲及弟弟生活了整整六个年头。那时的我能记起的东西不多,但还是模模糊糊记着一些事的。 记得房东家有几棵枣树,每当枣子快要成熟的时候,便和弟弟来到枣树下,双手合抱着树干使出吃奶得劲摇晃,那些拇指大的青枣纷纷掉落地上,随后赶紧蹲下捡起枣子不停地往嘴里送,紧接着又吐出来……开始几次,房东没有发现,不知哪一天,房东大妈捧着一捧枣子找上门来:琴子妈,您看这些枣子是不是两个孩子弄的?多可惜啊,还没熟呢,糟蹋了一地……房东大妈进门就絮絮叨叨地说着,妈妈赶紧搁下手里的活,连忙搬过一个凳子叫大妈坐下:她大妈,您先别生气,我来问问这俩孩子。没等妈妈发问,我和弟弟早已站在墙角低着头不作声了。妈妈见状,随手拿起炕笤帚上来就要打我和弟弟。房东大妈忙站起,拉过妈妈说道:琴子妈,您这是干嘛呀,怎么能打孩子呢,我过来就是和俩孩子说说,赶明儿别去摘了就行了。孩子还小,不懂事……大妈一边劝着妈妈,一边走到我和弟弟跟前笑着对我们说,枣子还没熟透,等熟了能吃了,大妈给你们摘了送来,好不好?看着慈祥的大妈,我和弟弟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其实,房东大妈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人,听妈妈讲,那几年她没少帮衬我们一家。那时,妈妈在团河农场上班,就把我和弟弟锁在家里,托付大妈抽空照料一下。大妈收拾完家务,就过来看看我们,有时还给我们拿来吃的,玩的。在这期间,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次,大妈捉了一只田鸡拿过来哄我们玩。那田鸡好玩极了,你碰它一下,它就跳一下,我和弟弟围着它满屋子转,玩得好开心啊。大妈走后,我们又玩了一阵,不知是玩累了,还是玩够了,记不清当时是我还是弟弟提出,将田鸡放在铁炉子上烤。我和弟弟紧靠在炉子边上光顾着烤田鸡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棉衣烤着了,都没察觉。直到房东大妈闻到烧焦的糊味,赶来把我和弟弟抱出来,扒下我的棉衣,用水把火浇灭,才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要说起小时候的趣事也真不少,记得有一次晚上妈妈准备带我和弟弟去剧院看电影,不巧,弟弟睡着了,妈妈怎么叫他都不醒,妈妈只好带我一个人去了,把弟弟一人锁在家里。等我和妈妈看完电影回来,发现弟弟趴着睡在了门外。北京早先的门是双扇开的,门锁上之后,无论是从里面还是从外面推都能有一个三四十公分缝隙,足够使一个小孩爬出来。妈妈赶紧把弟弟抱起来心疼地说道,妈妈真是太大意了,下次不会了,幸亏没事……这件事若是放在今天,没有哪位妈妈敢这么做,那时,妈妈太年轻了,没想那么多。心想,电影也就两个钟头散了,根本没想那个万一。 不知是哪年,好像是一九六二年吧,我们举家迁到黑龙江密山兴凯湖农场的一个码头砖厂。到那里的第二年,家里添了个妹妹。又过了两年,小妹妹也降生了。家里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父亲的肩上。父亲是个烧窑工,妈妈在砖厂上班,父亲母亲就靠那点微薄的工资养活着我们姐弟四人,实属不易。现在的人养一个孩子都费劲。我们当年是大孩儿看小孩儿,为这,我和弟弟也就成了“大人”。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父母上班走了,爸妈就把我们几个锁在家里,让我和弟弟看妹妹。外面没动静还好,只要外面有同龄的孩子嬉戏,我和弟弟就控制不住了,常常把妹妹强行哄睡后,从窗户跳下,加入到孩子们游戏中。估计爸妈快下班了,就又赶紧返回。可是那个时候哪个孩子不贪玩呢,赶上爸妈提前下班了,正好抓了个现行,不用说,一顿打是逃不了了。碰到这个时候,都是父亲做"坏人".就这样我和弟弟帮着父母一起度过了那难过的日子……那几年正赶上国家不好过,不过那时的我们,没有感觉到怎么苦,怎么吃不饱。就记着有一年冬天,爸爸从湖上冰窟窿里打上来一些像小指粗细的小刺鱼,炸了给我们几个孩子算是开了个洋荤。偶尔吃了几次玉米面菜团子。那时候,我们没有吃过现在的孩子吃的零食,没有玩过高级的玩具。我和弟妹的零食就是爸爸用沙子炒的玉米豆、黄豆,爸爸炒好后,每人给我们用酒瓶子装一瓶。就是这样的零食,我们还把它当作高级食品藏着,生怕被别人拿走。就连晚上睡觉也要抱着瓶子睡。所谓的玩具,就是爸爸烧窑时,用黄泥捏的小鸭子,经过烧制而成。再就是爸爸利用吃过的核桃壳自己制作的“猴子爬杆”。尽管这些简单的玩具,但在我和弟弟眼里是何等的珍贵好玩啊!同时很羡慕爸爸制作手艺之高。 兴凯湖是一个鱼米之乡。我们家就住在湖岸上。每当赶上渔汛期,妈妈都要带我和弟弟去水产公司买些鱼回来做给我们吃。水产公司的鱼的种类很多,什么鲶鱼、狗鱼、嘎子鱼、鲫鱼……最有乐趣的还是我和弟弟到离我们家不远的东边水闸的小河里用白条鱼逗龙虾上钩的情景。弟弟用一根细细的柳条将小鱼绑住,然后放在石头缝里,静静地等待龙虾来……还没等龙虾靠近小鱼,弟弟快速地将龙虾捉住。有时没等弟弟上手,我已把龙虾抓住,但竟被它像钳子的爪子夹住疼得我直叫,每每这时,都是弟弟上来把龙虾的爪子弄下来。弟弟捉龙虾比我有技巧。他两眼盯住龙虾,等待一个最佳时机,用拇指和食指夹住龙虾的头部一提,任凭它使出全身解数,也无回天之力。除了捉虾,我和弟弟还经常拿着鱼竿去小河边钓鱼,也十分有趣。那时候我们用的鱼饵是蚯蚓,鱼一般是好上钩的。不像现在的鱼,和人一样精,蚯蚓已不顶用了,都是自制的鱼饵。一次,我们又去钓鱼,碰上两个解放军叔叔也在钓鱼。不一会,叔叔走到我们面前,笑着问我和弟弟:小鬼,钓到鱼了吗?我们要回去了,这几条鱼给你们了。说着,他们把一个小网兜递给了我。我一看,里面有四五条巴掌大的鲫鱼。我拿在手里,瞅瞅弟弟,不知怎么办。妈妈常和我们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叔叔见我那个样子,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思,又说道,没关系,拿着吧,解放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嘛。听了叔叔的话,我点点头。那天不知什么原因,鱼就是不咬钩,真的没钓到鱼。要是没有解放军叔叔给的鱼,我们就要空手而归了。至今,我对那两个解放军叔叔还存有感激呢! 我的母亲是一九三八年九月初九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里,二十岁就嫁给了比她大八岁的父亲,并随父亲来到了北京。后又随父亲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农场。母亲虽出生在旧社会,但从小没有吃过苦,受过累,自跟了父亲后,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这里不光是来自生活方面,还来自政治方面的因素。因父亲的“错误”一家人都跟着受牵连。一九六六年,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年我刚刚十岁,上小学二年级。现在想起来那时极左的可笑。我记得有一天回家,突然对爸爸妈妈说,我要改名字。父亲说,名字能随便改吗?我随即争辩道,我们班里的同学们都改了,有的叫李革命,有的叫张政治,还有的叫……没等我说下去,父亲走开了。现在想来,当时他也的确和我这个孩子讲不清的,只得默默地走开了……文化大革命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一颗永不磨灭种子。那几年,我晚上睡觉时常做恶梦,醒来一头的冷汗。不是梦见红卫兵来抄家,就是梦见父亲被抓走。如果抄家时,发现你家的毛主席语录本上有折痕,或有手指印,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大堆“帽子”:对毛主席不忠了,反党反社会了……以致我工作后做了教师,我用过的书,本子特整洁,都是那时养成的“好习惯”。那个年代,我们一家不但要面临政治上的挤压,还要承受生活上的压力。 小的时候,我和弟弟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重担,常帮母亲干一些活计,来补贴家用。那时母亲在砖厂工作,春夏秋这三个季节制砖。冬天上冻了,制砖的工作就暂停下来搓草绳,草绳是用来打薄子。(薄子,即草苫子,就是用苇子或草用草绳编成的像帘子似的用来盖砖坯的。)有一年整个冬天母亲都在干搓草绳的活。搓草绳的材料用的是乌拉草。说起搓草绳,它属于一项技术活,虽说不是高科技,但确实有一点的技术含量。添草多少,用力大小,不同粗细的绳子有不同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在搓草绳前,首要选长一点的,软硬适中,色泽新鲜的乌拉草,然后,再把乌拉草用开水烫一下,目的是使之柔软,搓起来不伤手。但烫时,也要掌握好火候:过软,搓成的绳子质量不过关;过硬,搓起来容易伤到搓绳人的手,有时还会搓到掌心流血。这个活儿,领导允许母亲把乌拉草拿回家搓,但要求每天完成米,算一个工。母亲干起工作来一向认真,精益求精,因此,速度就要慢下来,米的任务当天很难完成。我和弟弟决定帮母亲一起搓。开始搓时,乌拉草在我们的两只小手来回磨合,可就是搓不出像样的绳子,母亲就示范给我们看,并给我们讲了搓绳的要点,我和弟弟随后就按母亲指教的要点去做,还别说,我们还真有悟性,一上午便学会了。我们不停地搓着搓着,一天下来,我和弟弟的小手都磨掉了一层皮,露出了鲜红的嫩肉。母亲见了,心疼地不准我们再搓了,可懂事的弟弟硬是要搓,我也就坚持着。说来也怪,往后再搓,手竟然没有再磨破过,真是万事开头难啊。 那时每天天一亮,母亲就让我们起床,吃了饭,便坐在炕上搓草绳。母亲看我和弟弟一天下来就是一个姿势,一个动作,挺单调的,很乏味,有时就给我们唱歌来调解一下气氛。她最爱唱的就是那首《劳动最光荣》,偶尔也唱她喜欢的歌:《我爱我的台湾》。母亲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有时唱到伤感的地方,竟落下泪来。就这样,我和弟弟在这样的氛围中,经过一冬的辛苦,终于搓草绳的活结束了。母亲把一冬天的“成果”交给领导时,领导很满意。的确,我们搓的绳子粗细均匀,接口隐蔽。领导的表扬令母亲很高兴,自然,我和弟弟也十分高兴。那时,为了让母亲下班回来多歇歇,我还学会了做饭。尽管切得土豆丝、面条有手指粗,可母亲回来能吃口现成饭,很是知足。不过,我焖米饭是最拿手的,火候掌握得极好,从没糊过锅底。这就要看烧火的功底了。先在锅里添上适量的水,然后把米下到锅里,等开锅了,就要改小火烧,烧至水要干了,把火灭了,用锅底的余火慢慢地将锅里的水分靠干。这样焖出来的米饭既香又柔软口感好。为此,母亲常夸奖我。弟弟也不示弱。我这个弟弟小时候特能干,家里的柴火多半都是我和弟弟到湖里割来的。我们配合默契,要么弟弟割,我捆捆。要么我们俩一起割,然后再一起捆。捆柴火的绳索就地取材,就是搓草绳用的乌拉草。割一小把乌拉草,用两只手反拧几下,然后就把一抱柴火捆上了,特麻利。 兴凯湖有我太多的回忆。那里留下了我太多的童年的乐趣。每到夏天,我和弟弟就到湖边不是钓鱼,就是捡贝壳和鹅卵石子。我们把捡来的贝壳拿回家,母亲给我们用线穿起来,当项链戴。记得我和弟弟还从湖边捡到过一个圆圆的透明的近似琥珀式样的东西,如获至宝。当时,那是我们最好、最贵重的玩具了。后来因搬家不知去向。别看我是个女孩子,跟着弟弟常在湖边玩,久而久之,我的性格和男孩子一样胆大。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年夏天,和弟弟到湖上船上玩,差点命悬一线。那天,开始我们是在岸边玩的,早先爸爸妈妈就嘱咐过我们,千万别到水里去玩。谁知,玩了没一会儿,我们看见距离湖边不远的湖上有两只船——一只大船拴着一只小船。那时,我和弟弟不知怎么上的大船,这个细节我实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上了大船后玩了一会儿,我还想到小船上去玩,一只脚刚踩到小船的舷上,没料到这只脚起到了撑杆的作用,小船一下子离开了大船,慌忙中我赶紧用双手死死的抓住大船的船舷,因此,被吊在两船的缝隙间,下身大部分在水里。小船也上不去,大船更上不去,进退两难。那时,只要我一松手,危险即将发生。我一面用劲抓住船舷,一面拼命的喊救命啊救命!弟弟听到我的喊声,跑过来抓住我的一只手,使出吃奶的劲,把我拉到船上。那天,我和弟弟不敢回家,因为我的衣服裤子全湿了,回去免不了挨一顿揍。我们只好等衣服晒干了,再回去。幸好,爸爸妈妈一忙乎,竟没注意我们那天的遭遇。直到今天,弟弟一想起此事,还在说:姐,是我救了你一条命啊! 一九六九年四月,因当年中苏关系紧张,我们全家又迁到宝清县农场三分场二队。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了我们家的终点站,再也没挪过地方。刚到队时,真有些不习惯:房子是土坯的矮矮的。完全比不上我们兴凯湖的高大的红砖瓦房,房子的建筑设计近似于北京的四合院。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没大米吃,主粮是白面。因父亲母亲是四川人,喜欢吃米,所以,我和弟妹的生活习惯也就随父母了,也喜欢吃米。那时,我整天和母亲吵着要米饭吃,母亲总是哄着我们说,这里不是兴凯湖,不种大米。等叫你爸爸找找看,附近的农场有没有种水稻的。回想起我们在兴凯湖住时,一切生活供应都按北京的政策,所以当年我们也就没有感觉到三年自然灾害的苦。不久,我们的生活渐渐地步入了正轨:爸爸仍旧干他的老本行--烧窑工。妈妈在大集体队里工作(当时,妈妈不是职工。)我和弟弟进了队里的小学,不知何原因,我和弟弟在原来的年级上都跳了一级,弟弟上三年级,我上四年级。可在大人们的眼里,说我和弟弟聪明,每每这时,听起来心里还是蛮舒服的。现在想来,当年跳级,我觉得是学制的问题。刚来一个生疏的地方,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记得,队里的职工,每年冬天取暖的煤及一年做饭烧的柴火都是队里统一拉到家,每户一车。西瓜、香瓜、葵花籽也按户分一些,那感觉真有点共产主义社会。至今想起来好向往啊。不过,每年按户拉的柴火,不够烧的,可自己再去筹备。我们家的柴火有一部分是我和弟弟去地里一背一背背回来的。要不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呢,的确是这样。你看,我弟弟每次背回来的柴火,无论是豆秸还是麦秸,走在路上,远远地看去,根本看不见人,只看到像一个小草垛在动,那不是一般的能干,那时,在我们二队是出了名的。别人见了父亲便夸:老王,你家的儿子可真能干啊。可父亲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忍心让孩子这样干。曾多次告诉我们不要背了。但弟弟很倔强,继续背着,为的是减轻父母的重担。赶上有月亮的晚上,我和弟弟还会约上好伙伴述莲一同去地里背豆秸,那月亮好圆好亮啊,照在我们身上,地上的影子,在慢慢移动……我们都在享受那劳动后收获的喜悦,一点都不感到累。 童年有趣的事很多,但记起的只有这些。可能是这些事深深触动过我,以致难以忘却。
(在线责编 尚书)
王秀琴,退休教师。年4月18日出生于北京昌平区。大专文凭,毕业于佳木斯教育学院。退休前是黑龙江双鸭山市宝清县农场小学教师。任教期间,辅导小学生作文多次在农场、省级、国家级获优秀教师辅导奖。爱好写作,文章多数发在知青网。曾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中央级综合性月刊)举办的全国征文中,撰写的《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获三等奖。
推荐阅读
梁晓声|母亲
贾平凹|怀念金铮
王剑冰|退出历史视线的那个商人
鲍尔吉·原野|向日葵的影子(外一篇)
毕淑敏|孝心无价
廖静仁|明德师傅(小说)
张 镭|我害怕活
陈小燕|不肯红的叶
周树山|罗锅四舅
秦 汉|斑斓之秋
罗永春|巴彦赋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