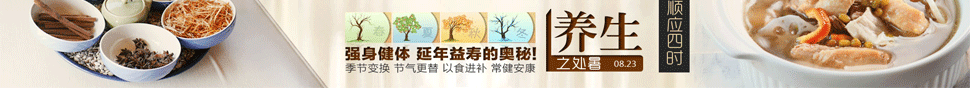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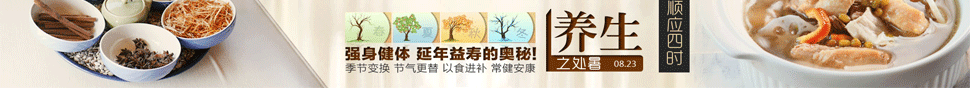
中国西部文苑
河曲的记忆
河曲的记忆
文/陈正奇
我是西安市灞桥区新合街办陈家村人。在我的印象中,古老的陈家村有一条由西南流向东南的小河。因河水不大,类似农村浇地的大水渠,故老一辈人都叫它河渠儿。我疑是河曲(渠)的儿化音,便将它写成河曲,意思是河道在此弯弯曲曲。
后来我从《灞桥区志》上看到,这条小河是年因灞河发大水(决堤)留下的痕迹。按志书记载,年灞河北岸从豁口村西决口,汹涌的灞河由此一路向北冲了下去,一泄数十里,在新合漕渠的米家和田家之间形成马沟(或许是马沟在此前已经形成,我不得而知),从肖闫村西到杜家村西北约2~米处碑楼附近向东,在陈家村地界上由西南流向东南,到丁家庄子与郭家村之间时河岸忽然开阔,形成一个潭。小河一路由此继续东北向,在侯家与苏家之间流过,在耿镇彭家附近注入渭河。
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在马沟北端,漕渠小学西北打了一眼自流井,为即将断流的小河增添了水源,这条小河才延续到70年代初。
说起河曲(渠)这个地方,实际是指小河在陈家村东南向北流再拐向东这段河道的拐弯处,大约有一千米多。这里的河道长满了芦苇,中间一条细细的河流,清澈见底,河里生长着各种的水草,水芹菜最为茂盛。河里常见有小鱼、小虾、泥鳅、黄鳝,偶尔见绵娃鱼(即鲶鱼)、刺拐子(黄拉丁鱼)、鳖(王八)和螃蟹等,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水生物。
记忆中的河曲,从今天的认知水平看,是受地形的影响。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出陈家村东头向南约米处有一墩塔,高约二三丈。村民传说小河发大水时,从村东南向北冲来,大有冲进村之势。有高人指点说在村子东南修一座墩塔,即可镇住水势,又可将河水逼向东方。现在看来修墩塔是史实,小河之水向东流,最终注入渭河,是因这里的地形地势决定的。
河曲的地形在河道拐弯处形成左边滩地,右边是河流。滩地长满芦苇。到深秋隆冬之际芦苇收割之后,可做成农家盖房时垫瓦使用的箔子或者编织成炕上铺的蓆子。小时候记得祖母曾经说过,解放前我家在河曲(渠)还有八分芋子地(关中人把芦苇称芋子)。收割下的芦苇打成箔子或编成蓆子出售后贴补家用。祖父还在蒋家集(今称耿镇),曾用一捆箔子换回一个风箱,还交了一个会做风箱的木匠朋友,我叫他屈师爷,两家人从此成了亲戚。
河曲的春天,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最惹眼的是满河道的芦苇像雨后春笋更像长矛的尖头从地里冒了出来,露出尖锐的雄姿。窝了一个冬天的花、草在春风的撩拨下昂首挺胸,伸长腰身,展开花蕾。雀卧丹(一种野草,顺地长,乡人称它雀卧丹)开的是蓝花,有点像苜蓿花;麦瓶花,其叶形似小麦,其花状如花瓶,花色粉红,故称麦瓶花;打碗花,蔓生植物,花色粉红,状如喇叭;刺堇,叶宽长边带刺而得名,有止血功能,花形像个绒球。《诗经》有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说的就是这种草。碗碗菜,其茎细长而叶宽大,叶子四周向上翘起,形似小碗而得名。最常见的是荠荠菜,蒲公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草夹杂在芦苇的茅头之间,跃跃欲试,呈现出勃勃生机。
燕子来了,沿着河道来回飞翔,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十分养眼。尤其是晴日的春光里,大妈、大婶都把捂了一个冬天的脏衣服,甚至将拆洗下来的被褥都拿到河曲来洗。那时没有洗洁剂,全靠捣碎了的皂角去污。然后把洗净的衣服被褥里面,凉晒在一尺高的芦苇上,远看一片五颜六色。
初春,河曲的水是冰凉的,人不敢直接下去。眼看着清澈见底的河里伴随着水草飘动的鱼儿,在水草之间游来游去而无可奈何!于是学着大人的样子,干起了小猫钓鱼的勾当。没钱买鱼钩就用母亲或祖母的缝纫针做一个鱼钩。先用煤油灯将针中间烧软,再用钳子将针弯成鱼钩的形状,最后找一根硬竹竿做鱼竿,简单的渔具就做成了;然后给鱼钩宽上蚯蚓就可以直接钓鱼了。没成想,这样简陋的渔具,我竟然在河曲通往郭家的小桥下边钓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鳖,还引起同伙羡慕的目光……
到了夏天,河曲成了儿童的乐园。河曲在向东流了大约一里许的地方,河道忽然变宽,在丁家庄子和郭家村之间形成一个潭。潭水深1米左右,面积有一亩地大小,从七八岁的孩童到十五六岁的大半小子,都聚到潭里戏水玩耍。
伏天的午后,河曲是最热闹的地方。在潭里戏水我们称之下河。关中人把下念“ha”。这些下河的男孩子有陈家的、丁家的,也有郭家的、苏家的。他们走到潭边,脱去短裤,像下饺子一般跳到潭里,直玩到黄昏才回家。
大男孩在深水区游泳,或狗刨窝(蛙泳),或漂黄瓜(仰泳),或双划(蝶泳),各取所需,尽显其能。小男孩不敢到深水里去,就抓住岸边,用两只脚击打水面,溅起层层浪花……
打水仗是大小孩子都喜欢玩的游戏。他们在水里或一对一,或二对二,或者一人对数人,玩的不亦乐乎。最为壮观的是,一对数人的水仗,煞是好看。只见一人站在水中间,周围数人攻之。四周之人都将手掌手指分开,掌心向下,呈半空掌状,猛击水面,水如注状,冲向中间人。而中间人则用双手划击水面,水在空中形成弧形水幕,罩住自己,既挡住了进攻者,又射向周围的进攻者,仿佛冷兵器时代的大将军舞枪弄棒,煞是威风。
在潭水里玩游戏,经常忘乎所以,也就酿成了大祸。有一次我在潭里戏水追逐小朋友时,脚下被人恶意扔下打碎的玻璃瓶底划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如注,被一个叫闰生的小朋友背了回家。
河曲捞鱼,是一件最有乐趣的事。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娃娃每人都提着或背着一个笼,借口给家里拾柴或者挑菜,在河曲二三人一组合,一人在前边用绳子或裤带牵着笼梁向前走,后边一人压着笼沿入水着河床底,一人在旁边观察看鱼是否进入了笼。就这样在河里来回拉着,往往还小有收获,能捞到小鱼、小虾,有时候还有金鱼入笼。捞的更多的是草鱼,我们叫他剑条子。我们把小金鱼装进瓶子,盛满水,五颜六色的,十分好看。可惜这些鱼,第二天因缺氧都死了。
天热了,十五六岁的大孩子,与我们的捕鱼方法不一样,他们则是在小河上选平缓地段,把两头一堵,在中间河道来回跑,把河水淌混,鱼被混水呛出水面,此时目标明确,或用笼捞,或用手抓,可以说是手到擒来。
最惬意的是有一年夏天,我们在潭里戏水,突然听到潭东边芦苇里有响声。原来芦苇荡里水很浅,大鱼在里面游不开。当我第一次看到一尺多长的大鱼时,紧张的不知所措,还有些害怕。在确认是鱼后,便静静地等待它再游过来时,然后悄悄用双手把鱼的头一下子按到淤泥里抓住。大鱼的尾巴在空中不停地摆动着,当鱼传到另一个小朋友手中时,他双手抱着鱼激动的喊着:“哎呀,哎呀,再逮一个就回家!”数十年后,我们见面说到这个场面,大家都会心的哈哈大笑。
夏天有时也下连阴雨,几天雨后,河曲又是另一番景象。大人、小孩都涌向河曲捡地软。来到河曲的男男女女,有的拿着小条帚,小簸箕,有的提着小篮子,在河曲的杂草丛里寻找黑褐色、软乎乎的地软。地软属菌类,有人说它是羊粪蛋外包的粘液,经雨水长期浸泡形成的。我没有考证真伪,但地软好吃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的地软炒鸡蛋、地软包子都是很受广大食客的欢迎的。那时大人、小孩都把捡来的地软,用河水淘尽、晾干,储藏到过年时蒸包子。
秋天来了,河曲一片枯黄,然而,也有让人动心的场景。鸟儿落在芦苇上,将芦苇压弯了腰,像个大弓,鸟儿飞走后,弯了腰的芦苇又反弹回来。抖落了的芦花,漫天飞舞,仿佛暮春时节的柳花飞絮,纷纷扬扬,好一幅“灞柳飞雪”图。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致谢!
本期责任编辑:伏萍
作者简介
陈正奇,灞桥人,无党派人士,西安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年12月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年1月毕业,获学士学位。年至年5月在西安黄河机械厂子弟中学教书,由初中到高中,由历史教师到历史地理教研组长,所带86级文科班学生全部考入大学。年5月调入西安教育学院,由历史教师而教研室主任,而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4年西安教育学院和西安联合大学合并为西安文理学院后,先后任历史系系主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唐都学刊》主编,《西安文理学院(社科版,自科版)》主编,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陈正奇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农学史,中国传统文化,西安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有《长安农事拾遗》《长安学人评传》《隋唐长安城文化管窥》《华夏文明纵横论》等:译著有《鉴真大师与唐文化东传》:主编有《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程》《陕西省情教育》(1—8册)《秦岭四库·智库》。
陈正奇教授长期兼任陕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安古都学会副会长等职。9年荣获全国高校学报优秀主编称号,年荣获陕西省高校学报“十佳主编”称号,年荣获全国教育学会优秀科研论文一等奖。
组织机构人员
顾问:周养俊
艺术指导:陈若星王芳闻
总编:伏萍
责任编辑:萧萧心语
理事单位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qiuyina.com/lkyt/94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