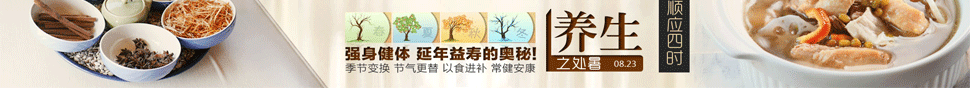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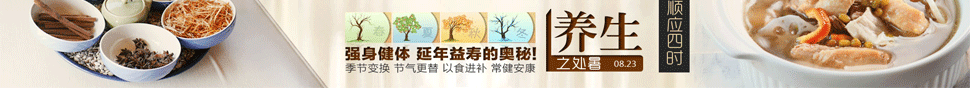
《圭臬》随笔
有关文学的扯淡,或诗歌的基本面
□成都凸凹
1
当我得知这首成熟的诗作是90后女孩宋欤焉十几岁的手笔时无比惊讶,当我又得知现就读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宋欤焉是宋渠的千金就无比不惊讶了。家学、教养血脉的打通,带动文脉、气质的贯通,正常了。正是这种贯通,让宋欤焉自知、景从、自觉,在一个习惯的下午写下《致QW及你们的诗》向自己的父亲和叔父——著名的宋氏兄弟——致敬。
《以母亲的口吻叙述遗忘》却有另一番景观。往小的说,它是作者对时间与生命的个人化理解与天才般的感悟;往大的说,是作者以自己的时间观、生命观来达成对存在世界的妥协与和解。这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遗忘之书”。
不疾不徐的叙述,不亏不盈的给出,节节俭俭前行,然后,一个变化:顿足、回身,或轻轻一跳。——我喜欢这样的语境,和文字的阴谋术。
如果说《致QW及你们的诗》因沉迷于父辈的迷宫而走失了一部分诗的真玉,那《以母亲的口吻叙述遗忘》的跟进则无疑是加倍的补还。肯定还会有人说看不懂这首诗,那也没关系,看不懂就看不懂吧,因为诗是允许一部分乃至大部分人看不懂的,只要有感觉就OK了。退一步,没感觉也允许,那只能说明你与这首诗无缘,或者你压根就是一个十足的诗歌白痴。
2
于庸常中发现蓝色闪电,于司空见惯中见到玉麒麟,这是诗人的本领。于白纸上咏出色彩,于汉字和想象中捉到画面,这是画家的本能。刘小萍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所以她做得很好,比如这首《太阳好阳》就是例子。
读这首诗,特别觉得作者就是文字的魔术师。道具就是这一二十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古老的方块汉字。
这位魔术师,不仅变出了好看的立体画,还变出了好听的天籁音,更变出了天人合一、万物生长、道法自然的美好、圆融而空明的忘我境界。
3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摸诗至今已有30余年,怎么着都算得上老江湖了。作为见多识广见惯不惊的老江湖,见过各种玩法的诗,当然也见过走狠一类的诗,但读了刘小萍《为一具尸体化妆》还是暗暗吃了惊。一个活人给一个死人化妆,化得那么精美那么细致入微,化到最后我们才知道,是“活着的我在为死去的我化妆”。真是敢想又敢写,且写得吓人一跳久而不宁。
只认文本不认作者性别是句自欺欺人的屁话。女就是女,男就是男,咋能不分彼此混为一谈呢。不错,《为一具尸体化妆》是一首好诗,因为它是由一只女手写出的。
4
刘小萍有多种诗写路数,又写了好些不同式样不同题材的诗,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她写的那一大批乡村人物志的诗,比如这首《周丫妹儿》。
诗歌天马行空无中生有飞扬跋扈,绝对属于虚构的体式。但《周丫妹儿》却是非虚构的。一首三四十行的诗,不光呈观了一个人悲凉的一生,还结具了一部长篇的体量与气场。全诗结构考究,语言干净,零度叙述的冰层下扣压巨鲸搏海的惊涛骇浪。
不唯《周丫妹儿》,《段超妹儿》《温包子》《外公》《兜兜菜》《张书玉》等都有这种特质与性能。
这种诗考验的除了情绪的把持,还考验着作者选材裁剪的美学原则,以及用词的精度,而刘小萍对此恰恰轻车熟路如探囊取物。
5
但凡是人都有与祖先、与血脉的源头对话的渴望,现在,这个渴望被吕历的《油灯》点亮了一一点亮成了光阴的故事。
6
余修霞《搁浅在麦地》是一首典型的“乡愁诗”。因为寄居城市一场突袭的暴雨以及由此形成的水灾,作者睹物而思涌,立马担心起了远方的故乡尤其故乡的麦子,立马铺排开了自己的诗歌情感。我看见的这首诗,就是这样一个情状。
这样的一个情状,当然是一种正常的情状,而诗的宪法要求的是不正常。余修霞当然知明这个道理,于是,在铺排得都让人为她捏把汗时,她刹车了一一她用几句特别有诗的漂亮句子打破正常,建构不正常,引来天光:“还有,让我揪心的小麦/不知道洪水欺负它们没有/我想换辆车,在芒种之前回到故乡/搁浅在麦地上,成为六月的小麦/让镰刀割走残留在体内的城市/那样,我就永远和麦地挨得很近”。
局部的胜利,有时是可以逆转定势和全局的。
再说一下长在作者诗地里的小麦。小麦当然是小麦,但也可以不是小麦。如果作者是位背井离乡的男性,我首先想到的小麦大约是他的青梅竹马的乡村少女。但作者是女性,于是,小麦在我这里就变脸为了摇曳在乡村的一株美好的物事,或者直接就是浩荡无边细如针尖的乡愁。
7
华子用《我之将死》巧妙、从容地解决和释放了怎样用诗歌处理面对死亡的态度问题。
8
印子君《今夜,我带你去丹麦》有一种急智的美学逻辑,和开阔的童话想象,让诗歌这种在不可能中求可能的艺术获得了明亮而欢悦的展形。
9
我老家有句俗语,叫做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这句俗语,用到至高无上的高雅的诗歌身上,也是合适的。就是说,写诗怎么写,没有定规,没有王法。
如果只把诗的写法分成巧写与硬写两类的话,我认为也是成立的。巧写可以写出好诗,硬写也可以写出好诗。
印子君的大部分诗,包括这首《今夜,我带你去丹麦》,当属走巧的一类。胡冬《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则属于硬写一类。其实,虽则是不同的写作招式,我还是有理由认为,印子君这首坐火车去丹麦诗,与胡冬乘慢船去巴黎诗,有一种互文关系。
丹麦,按说是与我们的生活空间两不搭界的地方,囿于种种本因,我们很难想到坐火车去一趟远在地球西边的丹麦。但是,诗人不理这个茬。诗人说,我们可以去的。诗人又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只有今夜”才可以去,“只有今夜”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绝决、极端、偏执,这就是诗一一就是这首诗拋出的专钓你的饵。你只能上钩。上钩了,你还觉得上得蛮舒服,因为沿圣诞老人、雪和安徒生童话这条逻辑线路,你的确可以去一趟丹麦。
整个诗,都是印子君使巧劲、用奇思布下的局。有了这个局的设计规划,再用诗的叙述语言落地坐实,诗就成了。
诗就是做不可能的事,变不可能为可能。
诗后落上日期再正常不过,但对这样的一首猜谜似的诗来说,不落“12月25日夜”这个日期,谜底埋得更深。
10
三首都非常一般,相较之,我荐苏唐果的《爱一个人就把他推入大海》,理由是它有些新意和极端而绝决的表态。
11
读《针》,我们瞥见的是一颗针在岁月中的穿行术,但内里却是写的针主。就是说,这是一首对慈母的赞美诗。针不过是喻体罢了。
诗中的针,是针,又不完全是针。是什么呢?作者不会明说和说明,我也不会,因为说了这个就漏了那个,不说才是什么都说了。要知道,因模糊美导致的误读、歧读,因误读歧读促成的再创作、多言路和广覆盖,正是诗的美学征候之一。
古往今来,写母亲缝衣针的诗可谓多矣,唐人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就是著名的一首。写诗其实也是一种博弈,与所有诗人博,甚至与自己博,博出一首与众不同而又折服人众的诗。依此看来,作者选择这个题材是顶着巨大压力的,可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针》一路写下来,写得细碎、完整、结实,诗意缤纷。即便如此,我对这首诗给定的评判也只能是:这是一首不错的诗。如果没有“每一缕经过的月光/都是母亲用过的线”这句神来之笔送来奇思、情怀、格局和境界,我就只能说这是一首正常的诗了。换言之,正是两行结句,挽救了这首诗。
张选虹既往的诗歌体式是有着较高辨识度的。这两年,他开始了“中年变法”,《针》即是其变法的一个案例。但变法、变革是有风险的,而他甘愿并正在冒着这个风险。
12
就文字中显出的智识而言,诗人要么是有着疯子皮囊的天才,要么是有着稚童皮囊的傻蛋,中间地带不属于诗人。两极呈现出的极端诗象,按说是相背的,远异的,有天壤之别,但事实非但不是这样,还正好相反。就是说,朝两个极端写出的诗,恰恰有着同一向度。要弄清、醒悟这个道理,读读印子君的《石经寺遇雪》就可以了。你可以说它是天才的高深偈语,也可以说它是小屁孩儿的天真独喃。但这就是诗,就是好诗。童心是印子君诗写创胜的不二杀手锏。
“龙泉山把一座古寺/藏得这么深,也被雪找到了。我跨进大院”,这个属于创意设定。设定完成后,随着几个含有双关意味的文化语汇——“皈依佛门”“招人喜欢”“投错了庙”——的渐进与转折,诗也就趋于完成了。
如果去掉最后两句“在神面前,我必须承认/自己六根不净”,让“投错了庙”成为结语,这首诗会更干净、空灵和余味无穷,个见。诗歌可以不总结,不下结论,不把一条路走到尽头。
13
考量一首诗的指标很多,并且各人有各人的圭臬。我以为,如果只用一个指标即把所有的指标打捆综合成唯一指标评价一首诗的话,这个指标就是场:气场。
我之所以荐孟松的《魔咒》,就因为《魔咒》制造并呈现出来的气场达到乃至高于了我心目中“诗”的气场——“诗”只有两种,好诗和差诗,但差诗不是诗,所以诗其实只有一种。气场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才艺渲染和情绪发散,是氛围的物理指代,这就要求,从开笔第一个字始,至收笔的最后一个字止,整个过程都是创气、养气、蓄气的过程,岔不得气的,写作者最好是一个喷嚏一声咳嗽都不该有。
当然,这首诗不光有场力颇强的气场,它还有很坚定的场向:它有永远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尊重所有生物生命的担当与立场。
最后提个建议供作者参考:因诗的题目已标为“魔咒”了,故让诗中不再出现“魔咒”二字会更有嚼劲和味道。
14
《蚯蚓之舞》写于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我独坐在龙泉山脚下,桃果在树上的风中轻摇,说些自己才懂的话。没有任何道理,我看着地面发呆。呆傻傻的,盲人聋者一般,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偏偏却看见听到了地表下的活物:蚯蚓。一条,又一条,很多条。它们在大地的内部,在泥土的天空,自由地干着一切想干的事。他们的干,在我看来,就是舞,那种身体扭出的很艺术的舞。我一下更傻了,傻得像了傻傻的蚯蚓。它们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做着人所不能之能事,做着任何动物所不能之能事。蚯蚓不管做什么,首先就是做排开泥土之事。我开始吟诗,准确地讲,是诗开始吟我。首先是借鸟排开混沌、遮蔽,之后是借鱼排开挤压、囚禁,再后是借人排开内讧和竞争。再后,一个转折,主角蚯蚓出场,排开土和大地。这是物质的层面。再后就是精神的界域了:排开地狱和亡灵。写到这里,有对比,有虚有实,就算结束了。结束了,也是一首诗,一首正常的诗。我在手机上写下了上面的诗句。殊不知,接下来,神来之笔出现了:把体内的骨头也排了出去。除了蚯蚓,没有哪种动物可以这样。蚯蚓的这种出动、作为与牺牲,这种信仰,多么绝决、彻底。想到这里,我亢奋不已,急忙写了出来!有了这进一层的一笔,模写是不可能的了。仅此,我要说,最好的诗,或真正的诗,绝不是写出的,而是偶遇的,也就是说,是神给的。这样的诗,可遇不可求,即是作者自己也无法写出第二首。
15
柴棚《你什么时候来看我》语言朴白、干净、稔熟;全诗气韵通顺,有很好的语感和词音;再加上抖出的三个“包袱”(实为转折)颇为自然且略有新意——故而,作为一首表达二人私情的小诗,是成立的。
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一首诗之所以为诗,至少在语言、声音和创意三方面达成共振。这首诗若想在诗格上有所扬升,就还需在开笔创意上做文章,但这又无疑会导致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因初设的基础已既定成那样了。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嘛。对了,除了前边说的三点,我以为诗的生成还应加上神性和思想这两点,否则,摆在那里的分行文字,只是分行文字,不是诗。
16
我荐,是因为他们爱:爱亲人、朋友、族人、人类、地球、宇宙和祖国;爱自己、爱和平。
我荐,是因为他们只听从内心一己之见的召唤,只遵循和膜拜诗歌的公共真理,而非其他任何势力与介入。
我荐,是因为他们已操持了只有诗人才拥有的、而又被我认同的诗歌技能与操守。
我荐,是因为我与他们的好脾性臭脾性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志同道合相濡以沬。
我荐,是因为我与他们同属一个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qiuyina.com/lkxn/8642.html


